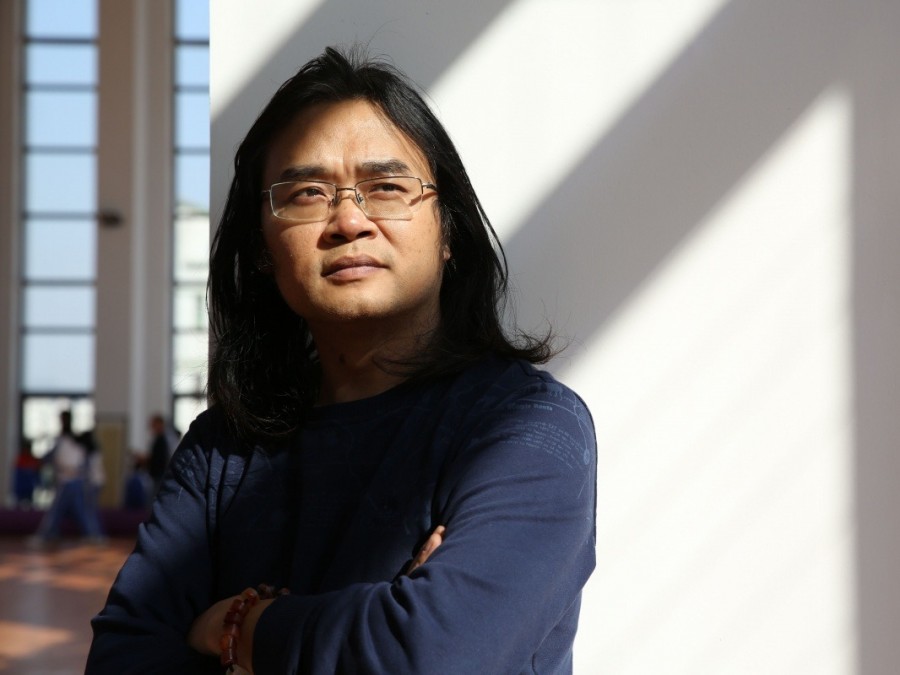潇湘诗会《远人读诗》(十二)丨返璞归真的爱,永不消逝
潇湘诗会·丝网 2019/12/20 14:23:48

作者丨聂鲁达
译文丨陈 实
没有永远的否,没有永远的是。胜利
在沙上留下消失的脚印。
我是穷人,天生要爱自己的同类。
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我爱你,我不传递也不卖荆棘。
也许有人知道我没有造过染血的
皇冠,知道我不喜欢诡计,
知道我确实以灵魂注满海潮。
我用鸽子补赎丑恶。
我不说“永不”,因为昨天
和今天与明天的我并不一样。
我以多变化的爱矢言真纯。
死亡只是遗忘的石头,
我爱你,吻你口中的幸福。
让我们捡些木头。让我们在山上生火。
当情感返璞归真
文丨远 人
出版于1959年的《一百首爱情十四行》是诗人的后期之作。时年五十五岁的聂鲁达早诗名稳固、著作等身,一举奠定他“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”地位的毕生代表作《诗歌总集》也在十年前问世。
纵观聂鲁达的毕生创作,最明显的主题有二,一是政治,二是情感。在聂鲁达笔下,两个领域的作品达到交融互织的地步。所以阅读聂鲁达,我们既读不到枯燥,也读不到浅薄。如果说,诗人二十一岁出版的《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》是他至今最负盛名的诗集的话,那么就只能说,是该部诗集的大胆与情感的澎湃将抒情诗推至一个令人目眩的高度,也是一位天才诗人所能达到的青春高度。在全球读者眼里,这部诗集带来的情感冲击很难有其他的抒情诗集能相提并论。但在时时具有创造性与突破性的诗人那里,即使自己不明言,也会感觉青春期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的遗憾。青春期有爆发力不假,更不假的是,爆发力不等于创作要求的全部,思想的成熟与对情感的丰富体认,会驱使诗人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想往投入实践。表面上看,这部《一百首爱情十四行》是聂鲁达为自己第三位妻子玛蒂尔德·乌鲁蒂亚而写,也未尝不可以说,它还是聂鲁达对早年名声太盛的诗集进行一次雄心勃勃的自我挑战。
这首以“没有永远的否,没有永远的是”开头的十四行是这部百首抒情诗集中的第七十八首。就诗的起句来看,我们能够体会,这样的句子还不可能出现在一个诗人的青春期作品当中。它蕴含的深意已经表明,这行诗携带的是诗人对人生的切肤体验。它是诗人早年不可能拥有的体验。对任何在青春期的人而言,激进与激情是最显著的常态。很多时候,青春也就等于激进与激情,所以,《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》无不充满聂鲁达天才型的个性涤荡。
只有当人对生活的认识随时间加深,激情转化为平缓,也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直接碰撞之后,“是”与“否”的对立才在了解人生的人那里得到统一。此刻的激情所现,虽比不上青春期的蓬勃,却多了青春期尚不具备的生活认识。所以,仅仅面对第一行,能发现聂鲁达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之后,对人与事的感受已具有哲学般的领悟,我们也就更能体味,诗人这部诗集在名义上是献给妻子,未尝不也是献给人生。
因此,说诗歌是情感的产物,不如说诗歌更是人生的产物。该诗紧接着的表述提供了进一步证明,“胜利/在沙上留下消失的脚印。”唯有经历人生,尤其像聂鲁达那样,不仅在思想上经历,更在自己多姿多彩的全球生活中经历,他才比常人有更多的理由相信,人生只是在经历中与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立场争斗。至于争斗的结果是不是有一个胜利?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。人类社会总在变化,在当时看起来胜利和正确的,未必到若干年后依然能证明是胜利或正确。
所有争斗的结局,都不过是“在沙上留下消失的脚印”。这里体现了聂鲁达非凡的人生感悟,我们决不能说“消失”属于虚无,只能说它属于真实。多少人的人生在事实上不可能留下痕迹。彼时的聂鲁达虽名震全球,在历史本身的冷酷与辉煌面前,还是感到自己人生深处的贫穷,一句“我是穷人,天生要爱自己的同类”,就说明聂鲁达对自我与人生有透彻的领悟。就思想而言,没有人敢说自己摆脱了“穷人”行列。人越是成熟,就越是从自命不凡走向对生命和情感的敬畏。从全诗第一段的开阔性来看,诗中的“你”决非妻子玛蒂尔德,而是更广义的、他以为的同类或人类。所以,说聂鲁达的这部诗集是献给人生,就在于他通过整部诗集的一首首推进,向更广阔的生活倾吐了自己的真挚心声和认识。
诗歌的确要求真挚。真挚不是想做到就能做到。在无数人的作品中,我们总不免看到林林总总的姿态和谎言。或许,以抒情为终生己任的聂鲁达比任何人都清楚,抒情若有姿态和谎言,呈现的就不是抒情。抒情的性质是坦率(谎言不可能始终坦率),所以他用最直白的言辞告诉读者,自己“没有造过染血的皇冠”“不喜欢诡计”,并以自己一生没遮蔽过的行为,总结自己的生活是“以灵魂注满海潮”以及“用鸽子补赎丑恶”。
正是有了这些“也许有人知道”的前提,有了这些常人难以拥有的经历和思索,聂鲁达才发现面对人生,没有人能说“永不”二字。对人类来说,肯定也好,否定也好,唯独永远无力承担。人有必死,也就不可能有永恒。更何况,诗人认识到的还包括“昨天/和今天与明天的我并不一样”。这是真实的感受,也是聂鲁达在毕生经历和思想中提炼的最属于人性的部分。从这里来看,聂鲁达已将诗歌的抒情性拓展到私人爱恋之外,到达哲理的制高点。也只有在这里,聂鲁达才真正完成抒情的脱胎换骨。所以,他坦承的“多变化的爱”具有直接的指认。往浅处说,是聂鲁达面对自己的数次婚姻;往深处说,则是人类中没有谁始终站在自己的情感原点。
放弃原点,是因为人生总要前行,哪怕简单的“我爱你”也不失一种动力构成。如何表现这一构成,聂鲁达的选择是“让我们捡些木头。让我们在山上生火”。行为看起来令人意外,在读者眼里,却有异常动人的力量。这是将人生洗尽铅华后的力量,也是返璞归真后的力量。人最需要的,也就是最后走到返璞归真的境地。当我们认真品读该诗,会在咀嚼中领悟,人生走过复杂,不过是为了到达简单。这是生活的要求,也是写作的要求。
诗人简介
巴勃罗·聂鲁达,智利当代著名诗人。他的一生有三个主题:爱情、诗歌和革命,因此他也是一位人民诗人和外交家,见证了祖国和拉丁美洲的历史。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其代表作有《十二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》《诗歌总集》等。

作者简介
远人,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有诗歌、小说、评论、散文等近千件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《大家》《花城》《随笔》《芙蓉》《天涯》《山花》《钟山》《书屋》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及数十种年度最佳选本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伤害》《秘道》《预感》,历史小说《卫青》《霍去病》,散文集《真实与戏拟》《新疆纪行》《寻找光明记忆》,评论随笔集《河床上的大地》《曾与先生相遇》,艺术随笔集《怎样读一幅画》(再版时更名为《怎样读一幅西方画》)《有画要说》《画廊札记》,人物研究《凡·高和燃烧的向日葵》,诗集《你交给我一个远方》《我走过一条隐秘的小径》《还原为石头的月亮》等。多次获奖,现居深圳。